1967年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李敦白已经达到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巅峰。这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8周年,李敦白坐在观礼台上,离毛泽东不到五十英尺,俯瞰十万挤在天安门前纪念国庆的人山人海。
李敦白是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仍然留在中国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他们中的更少数能够像他一样打入毛泽东的内部圈子,作为有价值的顾问服务于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值得信赖大使,甚至革命领袖。
除了李敦白,有奥地利的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共产党新四军医疗单位的指挥官; 来自波兰的记者爱泼斯坦,他担任着中国政府国际公共关系部门的领导; 还有伦敦出生的大卫·克鲁克,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院长。
虽然他们的背景大不相同,他们来到中国的动机也不尽相似,但是这些医生,作家和教育家却有一个共同点 – 他们都是犹太人。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离欧洲,在上海落脚避难,最终在他乡建立学校,犹太教堂和企业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大多在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后以犹太人离开中国而告终,在这个令人伤感的历史纪录上留下一个既干净又让人满意的结局,没有任何未了结的部分或难以回答的问题。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很多都留下来了,那些留在中国的犹太人中少数度过了戏剧性的生活,为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窥探早期的共产主义中国。
在曼哈顿服装区的心脏地带,有一栋没有窗户的大楼,大卫·克鲁克就在这里扛起一个艰苦繁重的工作 – 处理臭鼬皮,这当然不是这他进入中国对外服务最高层的道路上最显著也是最运气第一步。他的母亲,是一个住在伦敦郊区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的主妇,对他怀有更大的寄予。毕竟,他已经是一位展露头角的学生,而且已经通过考试被牛津大学接受。但在他有机会涉足于教室之前,家族事业崩溃,这场灾难过早地结束了他刚起步的学术生涯, 打碎了母亲的梦想。面对灰暗的前景和日益短缺的资金,克鲁克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学业开始工作,工作的机会是一个住在纽约从事皮货生意的远房亲戚提供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服装区为皮货商鞣制臭鼬毛皮和成为牛津一员是悬殊极大的,但这艰苦的经验确实让年轻克鲁克敏锐地洞察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对工人的困境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变革性的体验,将重新定义他的世界观和未来的走向。
跟克鲁克一样,李敦白在他的生命的早期对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也产生了深厚的同情,虽然他的背景并没有显示他将与矿工,砌砖工和管道工人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更看不出他在中国革命中会发挥中心作用。
李敦白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家族是查尔斯顿的犹太社区的重要成员,他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长大,跟工人和临时工没有任何的交集,虽然这些人会成为他以后为之战斗的目标。像克鲁克一样,李敦白是一名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也会取得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资格,但他也没有踏进校园。然而,李敦白未能进入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并不是因为家族的不幸,而是他有意识地拒绝了与自己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学校。李敦白认为, 由代表特权阶级的成员组成的精英大学提供的学术环境对他而言是非常不合适的,而当时的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参与工人罢工,甚至因为他的信仰和行动而被关进了监狱。
考虑李敦白的年龄和他的个人历史,人们也许会认为这种非正统的选择不过是青春期的叛逆行为,但是当李敦白的一生慢慢展现在人们眼前,他这种叛逆的倾向,严格遵守自己原则的个性成长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性格特征,总是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浮出水面并指导他做出最重要的决定。
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和致力于社会公民权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克鲁克李敦白的世界观,最终这个世界观将把他们带到中国,并帮助他们在最黑暗的日子中坚持不懈。
李敦白与中国的最初接触纯属巧合。在二战早期,他进入美国军队不久,李敦白得知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坐在教室里学习他一无所知的中文,真是具有讽刺意味。让新兵学习中文是军队在一个政治格局动荡并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建立资源,增加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战术。令他惊讶的是,李敦白发现,自己喜欢学习这种语言,并很快达到了熟练的程度,他取得了委派到中国的资格,并分配到在上海的工作小组。
1943李敦白看到的中国由于多年的经济动荡,外国势力的占领和迫在眉睫的内战阴影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赤贫和普通中国人的严峻生活形势让他震撼不已。他参与了当地的救援组织并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关注。他们派了个代表接近他,并向他提议:加入共产党的革命,并成为联络国外的代表,美国的李敦白当即就接受了邀请,但有一个条件 – 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克鲁克跟随中国的道路,同样的是一个巧合,但更加迂回。因为西班牙内战而受伤的克鲁克在马德里休养院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他读到了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新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描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当时的克鲁克已成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他来到西班牙是为了支持西班牙左派的势力。在那里,他被共产国际招募,目的是监视可疑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他阅读了斯诺的书之后,他被深深地启发,决定了他的命运将会与中国密不可分。为了去中国,他向自己的共产国际的处接头人提议让他去上海,他认为,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优势的地点,在那里他可以留意一些知名的托洛茨基主义成员并报告他们的活动。没多久,克鲁克便因为上海的种种具体情况而转移了注意力,让克格勃更沮丧的是,很快地他开始更注重修复障碍,却没有全心全力的从事间谍工作和情报收集任务。当托洛茨基在1940年被刺杀身亡,克格勃终于决定不再需要克鲁克的服务,并终止与他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漂泊和寻找其他就业机会,克鲁克最终开始了英语教学,并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员。
跟李敦白和克鲁克相反,罗森菲尔德和爱泼斯坦来到中国并不是为了探险和使命感的驱动,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逃离变得日益恶劣的生活条件,为了避免被一波又一波将他们的生命置于危机的席卷东欧的压迫浪潮的吞噬。
罗森菲尔德,毕业于维也纳著名的医学院,刚刚建立自己的诊所,作为一名产科医生的他刚走上一条有前途的事业之路,就在这个时候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并立即着手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国家。跟其他在维也纳的许多犹太专业人员一样,罗森菲尔德被迫关闭他的诊所,并最终被送到城外的劳改营,他的命运无可挽回。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罗森菲尔德将握着中国上海的签发的避难签证走出劳改营。 命运的变故实难预料,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不明确,但是我们也能合理的推测,罗森菲尔德能够引起何凤山的关注对他而言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何凤山是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他凭一己之力,通过有漏洞的规定发给奥地利的犹太人“难民”的签证(比如上海这些城市,他的政治系统和基础设施已被多年的动荡破坏),而从挽救了无数奥地利犹太人的生命。
跟上海类似,哈尔滨不仅是满洲中国广大东北地区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处于动荡的状态下。20世纪之交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扩展曾推动哈尔滨的快速发展,哈尔滨从一个远程交易前哨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的交通枢纽和对中国,俄罗斯和日本有战略价值的商业中心,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地陷入控制哈尔滨的权力之战中。战争带来的不安和混乱,导致了很多法律规则,政治惯例和社会规范的扭曲或彻底崩溃。这一系列的因素- 一个没有规范的交通枢纽 – 使哈尔滨成为吸引革命者,机会主义者和难民的目的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爱泼斯坦一家来到了哈尔滨,以为这将成为他们的避风港,让他们得以逃避正席卷波兰,威胁无数犹太人生命的,越来越可怕的大屠杀。刚来到哈尔滨不久,爱泼斯坦一家便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混乱和这个城市的居民 – 美国领事手持手枪光天化日之下漫步在街头,日本电影制片厂导演同时也是日本间谍,并留下可怕的杀人记录,中国军阀先开枪后提问的野蛮行径- 使爱泼斯坦的父母意识到,哈尔滨市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也不是一个适合一个年轻的家庭生长的地方。很快,他们就搬到了天津,一个繁华的港口,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东南方,今天离北京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车程。
在天津,爱泼斯坦接受了了英国学校的教育。在年轻的时候,他对新闻产生了兴趣,随着他年纪的增长,这个兴趣也逐渐变得浓厚。到了15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联合出版社的自由职业者。 为了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新闻事业,他最终不得不辍学,以便有充分的时间跨越中国北方,报道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也许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压迫和社会动荡,爱泼斯坦,就像克鲁克和李敦白一样,对他遇到的生活极为困难的中国人充满了同情,而这种同情在他父亲赫尔曼的教导下变得更为深厚,父亲曾训诫这位年轻的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忘了犹太人遭受的困境。
爱泼斯坦的新闻天赋和他在著书中表达的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吸引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的注意,后者将他至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宋庆龄是一个有远见的革命者,她认识到,中国寻求海外力量的成功将取决于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她开始着手寻找途径提高中国的形象。爱泼斯坦就是其中的一条道路。在她的鼓励下,他利用宋庆龄有影响力的关系网和大量的财政资源,启动了一系列广泛的宣传活动,针对在美国和欧洲的群众。爱泼斯坦作为总编辑的每月画报《今日中国》的建立正是这些努力的产物。但随着中国变得离西方越来越远,刊物有效地成为了(并保持)共产党传给外面的世界的声音。
在1949年共产党接管前夕,罗森菲尔德已经是中共军队的军官军衔,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一军衔是因为他已经证实了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领导者和医生,他不仅能救治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普通士兵的伤痛 ,更重要的是,他还能亲自照顾的资深革命者的需要, 这些人在以后的中国新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考虑到他的地位,罗森菲尔德享受这胜利的果实,以及他和他的中国同志一直在努力的回报。然而,讽刺的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大鼻医圣”,这是部队给他的昵称,决定回到家乡维也纳。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罗森菲尔德深信,奥地利已经开始恢复原状,他也能像以前那样的生活。而且他还打听到他的妹妹还活着,他渴望与她团聚。
共产党胜利前夕,克鲁克也在中国东北前线服务,运用自己的教学经验教育在战场上作战的青年领袖,这些人今后也会成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高级成员,他也为成立中国的外国语学院奠定了基础。克鲁克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并通过长期及大量的自我牺牲获得了共产党领导的信任,作为一名党员,他愿意服跟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忍受苛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克制,有时候这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克制比其他中国同志更为严厉。
众所周知,对中国人来说Rittenberg 就是“李敦白”, 李敦白在艰苦卓绝的500里长途跋涉去延安洞穴避难的过程中与毛泽东,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革命者并肩作战,也正是在这称为“长征”之途上他证明了自己的革命气概,并展示了他的革命热情。
在延安,像其他革命者一样,李敦白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都按照一个被限制的常规生活:白天,他是一个毛泽东的顾问,在美国政策上为毛提供见解,他代表毛泽东起草正式信函给杜鲁门总统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到了晚上,他是革命党人组织的重要舞会的积极参与者,参加舞会使他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影响力的成员建立了紧密和深厚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在他今后在中国的生活中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熟人便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她是一位女演员,李敦白认为,她的舞技比她的演技更好。有时候李敦白还担任劳莱和哈台电影的兼职翻译,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都喜欢在星期五晚上饭后看电影。
未来的30年李敦白将会上演属于他自己的跌宕起伏的古希腊悲剧:年轻激进的革命者傲视一切,急于改写历史,却被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生命的历史漩涡无情地湮没,命运的逆转将高高在上的他拉入深渊,在经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终于领悟,最终从无知到觉悟的转变。
自负
在20世纪60年代初,十年动乱,被称为伟大的人民文革的前夕,李敦白在中央广播局外事办工作,这是一个站在革命的前沿的,权力极大的组织,具有重要的战略性。而李敦白,一直忠于他的初心,在文革最初阶段积极地参与。他动员职工,组织革命学习班和其他相关活动,这使他一跃站到了革命领袖的位置。
下面一段文字是从他对全国各地的观众的演讲中摘录下来的 – 从小村庄的农民到礼堂的学生到体育馆的工人 – 他的演讲让他的声名鹊起,并把他变成一个知名人士:
“当我在美国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和钢铁工人,矿工一起肩并肩地工作。我当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所以我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地剥削劳动人民的。美国工人的生活艰难而困苦。中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随后作为革命的激进领导者他策划了接管中央广播局,这个大胆的计划让他的革命生涯达到了最巅峰。
被自己的权力和成功所鼓舞,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他的演讲技巧和声望质疑其他人对革命的忠贞度,并指出他们在行为上的矛盾,这种手段结束了许多无辜人的的职业生涯,并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诸多苦难。
命运的逆转
李敦白的其中一个中伤目标就是江青,李敦白在延安认识的熟人,他认为是二流演员和舞伴,在当时的情况下,江青对他根本无法构成威胁,要知道李敦白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很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人。事实证明,李敦白在这步棋上严重失算,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的倒台。延安以后,江青证明了她是一个有价值的女演员,她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白骨精”, 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头目,也是大众恐惧和厌恶的对象。李敦白将他的严厉指责指向了江青,这个已经是众多人恐惧和厌恶的对象 – 参考她的绰号,但是仅仅几个星期以后 – 李敦白发现自己被单独监禁在秦城监狱,北京郊区的一个惩教监狱,这个监狱也许没有恶魔岛那么可怕,但是却同样的臭名昭著。
大多数的反革命分子,教授和艺术家都在那里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谁都知道被送往秦城监狱生不如死。对于李敦白,在秦城监狱的时光却是一个反省和思考的岁月。监狱的生存之道,长时间的无法动弹和无处不在的沉默,李敦白觉得,这种存在跟在在“寺院出家静坐的和尚”没有什么不同,他强迫让自己保持头脑灵活,主动参与精神思考。 “李敦白同志,”监狱的监狱长曾经这样记录他的活动, “每天从早到晚都读 [人民日报] ,没有一次例外过。”
尽管他们是党的一员,在前线做出过牺牲,并且对国家和党都有无可挑剔的记录,克鲁克和爱泼斯坦也均在文革的高峰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对外国势力,阴谋和间谍的恐惧使他们成为了直接受害者。类似的命运降落在大部分的外国人身上。然而,跟其他被囚禁的外国人一样,克鲁克和爱泼斯坦在1973年被释放,并正式地被邀请到国宴上,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道歉。只有李敦白还处于失踪状态。当有人在晚宴上询问李敦白的所在时,周恩来严肃地回答:“李敦白自己已经承认自己对国家及其公民做下严重的罪行。正因为如此,他将继续留在监狱。”
豁然开朗和觉悟
李敦白的监狱期限延长了近六年的时间,1979年他被释放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更有智慧,更谦虚的人。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和犯罪事实后,他终于获得赦免。官方政府发表声明免除他的罪行,声明这样说到:
“自1945年以来李敦白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向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0年,李敦白,已经快要六十岁了,决定他与中国的纠缠已经到此结束,他想要回到这一场冒险开始的地方,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在那里,他成为了当地社区大学的老师,打算过上安静平和的生活。虽然他认为自己与中国的恩恩怨怨已经了结,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打算让他真正离开。
随着中国开放,并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大型美国公司也开始关心起这个巨大的,能带来的潜在的市场机会的国家。但由于中国已经关闭了多年,中国缺乏成功需要的见解和经验。李敦白具有丰富的中国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熟悉中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 – 其中许多人曾经是他在延安窑洞里肩并肩的战友 – 李敦白成为了任何美国公司认真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专门顾问。仅举几个例子,英特尔,李维斯和微软都相续敲开了他的房门。这个曾经因为相信共产主义而拒绝了资本主义的人现在却因为帮助共产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变得富有起来。
李敦白,克鲁克,爱泼斯坦和罗森菲尔德,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近了中国,每个人都在这个国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最终,却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让我们洞察到了他们的性格和动机。除开他们都是犹太人之外,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公民,而最有趣的是,他们都活到90多岁。他们的长寿跟他们和中国之间的接触到底有没有关系耐人寻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经验和贡献给予了世界一个独特有趣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20世纪的伟大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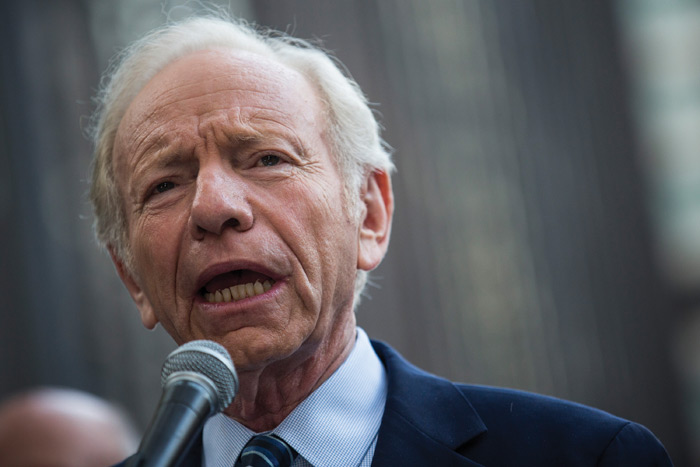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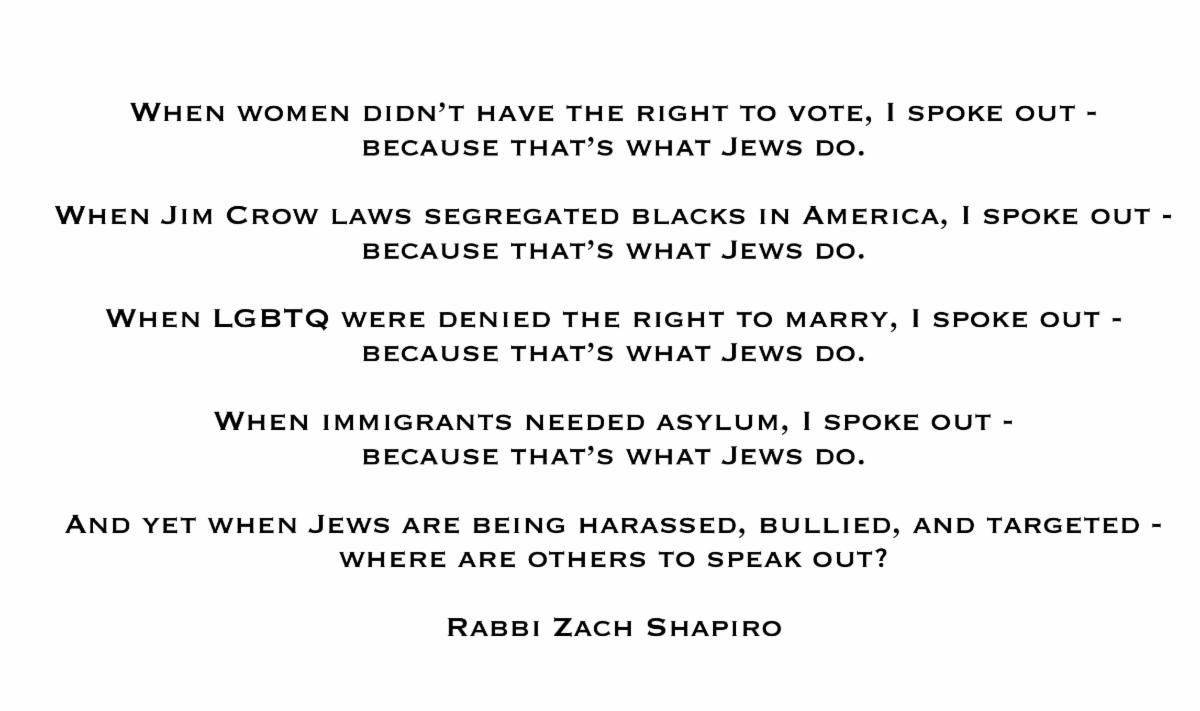










 More news and opinions than at a Shabbat dinner, right in your inbox.
More news and opinions than at a Shabbat dinner, right in your inbox.